先生们,今天是我第一次谈论生命的存在。先生们,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享受生命中那种强烈、即时而且新鲜的感受,今天,这种感受第一次使我欢欣鼓舞,快乐到几乎要哭。 我快乐是因为从来不曾有过那种感受。我鼓舞是因为以前没有感觉到生命存在。从来没有感觉到。谁要是说我有,那是谎话。他说谎,而他的谎话伤透我的心。我的欢欣源出于对个人探索生命的信念,没有人能够动摇这个信念,谁想这样做,他的舌头就会跌出来,他的骨头也会跌出来,他必须跑来跑去捡,冒着捡错别人骨头的险,才能够在我眼前站立。 从来没有生命存在过,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人经过,直到今天。从来没有房屋、街道、空气和地平线,直到今天。如果我的朋友佩里埃特此刻到来,我会说不认识他,说我们必须从头开始。到底我是什么时候结识佩里埃特的呢?今天是我们初次交上朋友。我会让他走,然后再回来看我,好像不认得我一样,那是说,第一次。 今天,什么人,什么东西,我都不认得了。我发现自己处身于一个陌生的国度,一切都有与生俱来的玲珑浮凸,有主显节那种永不暗淡的光。不,先生,别跟那位绅士说话。你并不认识他,无聊的攀谈会让他惊讶。别把你的脚放在那石子上:谁知道它并不是石,你会整个人落空。你要当心,因为我们正处身于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我活过的时间是多么短呀!我的诞生是那么近的事,没有什么度量单位可以计算我的年纪。我是刚刚出生的啊!我还不曾开始生活呢!先生们:我这么小,几乎容不下一天。 我从来没有听过手推车的噪音,直到今天,它们运送石头去筑豪斯曼路。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跟春天并排着走,一边说:“假如死亡是另一个样子……”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见过圣心教堂圆顶上金黄的阳光。直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小孩走过来用他的嘴巴深深注视我。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不知道有一扇门、另一扇门和远处雄壮的歌声。 别管我!生命已经让我看透自己的死亡。
Category: Literature
一条路 【日】东山魁夷
我心中有一条路。 这是夏天清晨野外的路。 每当我观看在青森县海岸牧场画下的素描时,眼前便浮现了这条路。这是一幅可以望及正面山冈灯塔的牧场的素描。从我想到不妨将那里的棚栏、牧马和灯塔去掉,只画一条路的时候起,这条路的影子就在我心中萦绕。 只有路的构图能成画吗?我惴惴不安。但是,除了路以外,我什么也不想入画了。我想画的,不是现实风景的路,而是象征世界的路。画的虽不是某一条具体的路,但一考虑到种种条件,我还是觉得以种差牧场的路为线索来构图似乎更好些。战前我曾将这牧场作了素描。这是十几年前的往事了。如今这条路的姿影果真依然如故吗?我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 纵令前往,不也是徒然吗?有时我也想,何必囿于那条路呢?那是1950年的事。那时候,旅行条件也不能说很好。然而,我惦挂的不是这个,而是倘使成为我最初依靠的现实风景面目全非了,那么,好不容易在我心中形成的那条路,会不会淡化了呢? 尽管如此,我无论如何也还是想前去看看。当时东北干线沿途因水灾不通车,我就乘奥羽线火车绕道青森,到达了八户。 前往种差海岸牧场的那条路,虽然荒芜,却依然如故,它穿过牧场,缓缓地向立着灯塔的山冈伸去。 “来对了。”我喃喃自语,一直站在那里。 一条路横躺在向大海倾斜的矮草丛生的斜坡上,路两侧长满了杂草,笔直而迟缓地向上延伸,刚刚稍向右拐,路便从视野中消失了。于是只见一条线——可以想象这是路的继续——横穿远方的山冈。 但是,浮现在我心中的路,同这条现实的路仍有相当的距离。作为草图,这山和路的组合似乎不错,然而如今横在眼前的路,在炎炎夏日的焦烤下,土和草都干了,路的土那种特有的沉静的感情、两侧青草和路接壤处那种细腻的情趣都丧失殆尽了。对面山冈以苍穹为背景映出的轮廓线,以前是很柔和的,如今顶上却露出了岩石。难道是十年的风雪洗刷出来的吗?令人感到战争的痕迹,就是在这奥洲边远牧场的路也表现出来了。 我想起了一条温润的饶有情趣的路。我说明了来意,在牧场歇了一宿,清晨趁太阳未露脸的时候,便画这条路。回到市川,每天早晨我都漫步在附近河提的路上,观察被露水濡湿了的草丛和泥土的颜色,仅作参考。就这样不断地做着创作《路》的准备工作。 路有两种,一种是回顾的已经走过来的路,一种是面对今后朝前走的路。我想画的是后者。而面对缓缓的上坡路时,我们就会产生一种今后朝前走的路的感觉。相反,俯视着下坡路,就容易感到这是在回顾一条已经走过来的路。 我创作这幅《路》时,在思考今后将走的路的过程中,有时也观望已经走过来的路。它是绝望和希望交织的路,既是漫游的尽头,同时也是一条崭新的路;是憧憬未来的路,又是怀念过去诱发乡愁的路。但画面上远方山冈上空显露的微明、路在远处向画面处朦胧消失的景色,就使得那种今后要走的路的感觉变得强烈起来了。 将人生比作路,是平凡的。但芭蕉的题为《奥州小路》的文章,是一篇不朽的游记。可以说芭蕉的这个篇名,既体现了他自己在偏僻的羊肠小路上穿梭旅行的身影,又象征着芭蕉的人生观、芭蕉的艺术观吧。我也经常旅行,在旅行中感受人生、感受艺术。那条象征性的路,已成为十分清晰的影像,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上。 我也走过各种各样的路。 在早春山冈的路上,我看见绿油油的条纹状麦地,未抽芽的桑田,远方崇山峻岭上的白雪,还有湛蓝的天空上飘浮的云朵。 旧街道沿溪流将几个寂静的山村联结起来,杉林的影子投在路上。两旁满是压着石头的木板房,昏暗的蚕棚,梭子的声响从窗口漫了出来。 往山毛棒、水枹树林的深处走去,是一条铺满落叶的路。踩在上面,脚心有一种软绵绵的感触。踩在落叶上,发出了声音。这里那里可见白树亭亭玉立。森林深处是一丛明朗的红枫。 雪国的路。我小心翼冀地在结满坚冰的路上行走。雪橇来了。因为靠边躲闪迎面而来的雪橇,我踉跄地踩进了深深的雪里。年轻女子的头巾,很是鲜艳夺目。 在古老的小城镇,从房檐流下了洁净的水。格子窗下摆满了花草盆。仓库那泥灰剥落的墙壁上,抹着明亮的夕阳。商店门前挂上了印有字号的帘子和古色古香的招牌。在雨中的都会柏油路上,橱窗流泻出绚丽的灯光。从地下室酒吧腾升起爵土乐的旋律。人们的面孔挂着疲惫,煞是寂寞。 学生们的学生帽带着新的美字徽章,他们从茸谷车站踏着落樱,穿过博物馆旁,走在通往学校的路上。 秋夜,美术馆的墙上公布了入选者的名单。昏暗中,人声杂沓。初次入选的喜悦,使我迈着恍如悬在空中的脚步,向坡下的邮局奔去——这是去给神户的双亲发电报。 骑着驴马的老人沿着城墙走了过来。村妇在石桥下洗溜衣物,不时用棍子敲打着。白杨树在风里摇曳。这是热河省的路。 罗马郊外的石板路,尽是废墟、丝柏和笠松。这是保罗看见基督幻影的路。天上飘忽着夏天的云,远方传来雷鸣。 成排的古老人字形房顶的屋宇。在城门钟塔上筑有鹳鸟巢。广场上置有喷泉。马车的马蹄踏在薄暮临近的石板路上,带着四射的火花走过来。这是波恩的古都。 为了去领取应征通知书,我出了品川车站,走在灯火管制下的黑暗的路上,这是雨后通向区公所的路。 到处都是发热的瓦砾、断落的电线、死马、黑烟。日食般的太阳。这是空袭下的熊本市的路。 拖着母亲的灵车行进在荆泽的路上。狂风劲吹。新雪闪烁的富土山浮现在清朗的天空下…… 路的回忆是无穷无尽的。今后会走什么样的路呢?舒伯特的歌曲集《冬之旅》就是为米勒的诗谱写的,全篇是描写冬季旅途上的旅人孤独的身影,歌唱了人生的寂寥。有名的《菩提树》这首歌,也是一串串美妙的诗句,是回忆乡愁的歌,回忆起漂泊的旅人,在城门旁喷泉边菩提树的叶影下找到了舒心适意的所在。还有《路标》,是描写在旷野徘徊的旅人发现了路标,但这是标志着许多人一去不复返的路。最后旅人来到了“旅馆”。这就是墓地。旅馆的标志,是送葬的蓝花,疲惫的身躯在冰冷的卧床上得到安息。可是,他遭到旅馆老板的拒绝,再次彷徨而去。这条路,是绝望的冬天的路。我走遍了冬天的路,好不容易才迈上了闪烁着初夏朝露的草原之路。 这年秋天,我将《路》作为参展作品,提供给了第六届日展。竖长的画面靠中间的地方,画了一条灰色里带些粉红色的路,左右的草丛和山冈是绿色,狭窄的天空是灰中带蓝。我考虑了这三种颜色分量的对比。作为参展作品,画面虽然显得很小,但如果画得比这再大些,画面的凝重感就会淡薄。我期望的是让这小小的画面充实起来。 我孜孜不倦、日积月累地精心作画,循序渐进完成了。 这一年,我第一次担任了日展的评演员。《路》这幅参展作品博得了许多观众的共鸣,在画坛上和社会上都得到了承认。 我在本书首章这样写道:在人生的旅途上会有许多歧路,与其说是按照我自己意志的驱使,不如说是一种更加巨大的外在力量驱动着我,这种想法至今未变。但在我心中早已培育了要走这条路的意志,所以这才形成这幅作品的吧。可以说,我的心灵一旦平静,我的方向也就相当清楚地固定下来了。这条既不是明朗的骄阳普照的路,也不是笼罩着凄惨的暗淡阴影的路,而是一条在清晨微明中,平静安详地呼吸着的、坦荡的、自由自在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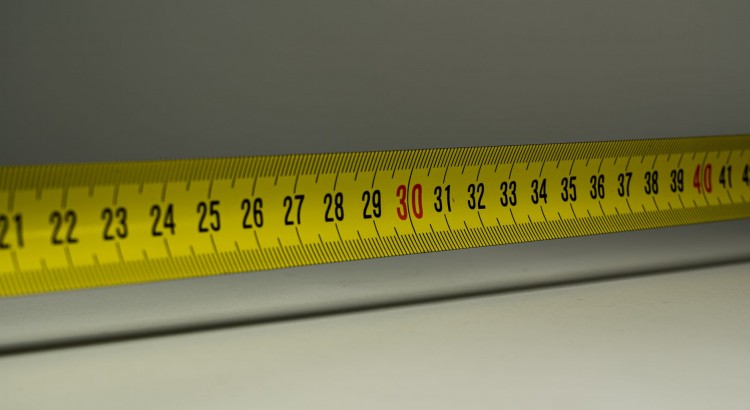
三十岁记感 【法】阿尔弗莱·德·缪塞
偏有一道忧郁的目光投向往昔,想去看看……那幻灭了的希望与埋葬了的痛苦,——偏有一道更忧郁的目光投向未来,想去看看……那人生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