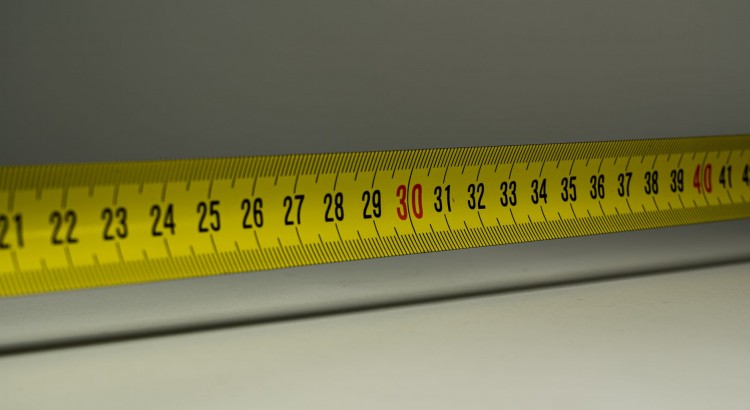偏有一道忧郁的目光投向往昔,想去看看……那幻灭了的希望与埋葬了的痛苦,——偏有一道更忧郁的目光投向未来,想去看看……那人生的冬天!
零碎的日记 【法】尤金·尤涅斯库
我究竟什么时候第一次注意到时间在“流逝”呢?我的时间感并非从一开始就同死亡的概念相连。当然在四五岁时,我就意识到自己将日趋苍老并最终死亡。七八岁时,我对自己说妈妈有朝一日会死的,这一想法令我惊恐万分。我明白她将在我之前死去。然而,在我看来那只是现在的一种终止,因为一切都是现在。一天、一个钟点在我看来都极为漫长,无边无际。我看不到它的终结。人们对我谈及中年时,我的感觉(或印象)是来年永不会到来。而在安德奈小教堂附近居住的那些日子里,我身处时间之外,即某种天堂之中。到了十一或十二岁,并非在此之前,我才开始获得终结感。我们有时间同外祖父,外祖母,萨比娜阿姨,还有母亲一起上苏弗伦大街上的小影剧院去。对我来说这可是某种异乎寻常的事。我急躁不安地等待着这样的欢乐时刻。外祖母是残疾人,我们用一辆轮椅车将她从阿弗勒街一直推到苏弗伦大街。当我们一起出发时,我忽然想到欢乐将无法持久,节目总会结束,最后我们还得回到家里,于是,我的欢乐之情便一下子黯然失色了。节目会持续很长时间,非常长的时间,两个甚至三个小时,但这样长的时间毕竟有尽头。正是等待使我感觉到了时间:倘若无所期待——期待欢乐,期待假日,期待圣诞节和星期四,期待星期天到巴黎郊外妈妈的一些朋友处游玩,我便无法感到幸福。 季节似乎在空间舒展,世界是道布景,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有时明时暗的缤纷色彩、时隐时现的格式花卉,而我们却身处时间之外,一动不动,观望着时间的流逝。也许,正因此故,某人的死亡在我看来显得神秘、残酷、不合逻辑;仿佛现时的一个真空。接着,蓦地发生了某种颠倒,彷佛一股离心力将我连同那些去了又来、来了又去的事物一道置放于我自己的稳定之外了。更糟的是,我猛然感到那些事物始终停留在原地,一动未动,倒是我在一步步远离它们。待到十五六岁时,现在消失了。从那时起,对我来说只存在过去和明天,一个已被感觉的如同过去的明天。 从那时起,我每天都努力想抓住某些稳定的事物,每天都拼命地试图重新找回一个现在,然后再加以护理、加以扩展。我开始旅行,为了寻觅一个时间无奈其何的完整无缺的世界。习惯磨砺了时间,擦亮了时间,并像在打蜡地板上似的滑行在实践的表面。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永远崭新的世界,一个永远永远年轻的世界,这景象意味着天堂。速度不仅犹如地狱一般,它就是地狱,是自由坠落的加速。现在已逝,时间已逝,不再有现在,也不再有时间,几何级数的坠落将我们抛入虚无之中。 从我出生之日起,一些时间流逝了。 很多同时又是很少的时间流逝了。我至今尚未理解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我只剩下很少的的时间来理解我尚未理解的一切,而且我也丝毫不认为我最终会获得成功。我甚至尚未能够接受生存、接受我自己。除却包围着我的生物和事物外,我一无所见。这些事物在我看来就像一些谜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很难同许多人沟通,或者根本无法沟通,或者很少能够沟通,因为我同自己都难以沟通。为了充实生活、充实真实、充实思恋,我寻找并获得的那些赏心乐事有时(可惜极少)成功地遮掩了生存的丑恶。它们曾经给予我快乐,然而此时我已无能为力了。痛苦、磨难、失败在我看来总是比成功和欢乐更为真实可信。我一直努力生活,但一生都在生活的侧旁活着。我想大多数人均有同感。我始终不知如何忘却自我。为了忘却自我,我不禁必须忘却自己的死亡,而且必须忘却我所爱的人们的死亡,必须忘却世界的终结。终结的概念令我惊恐万分,使我神经错乱。唯有酩酊大醉时,我才感到真正的幸福。遗憾的是酒精扼杀记忆,而我的欢乐中除去一些模糊的回忆已毫无保留。生命是个恶时辰,可这并不妨碍我爱生命胜于死亡。爱生存胜于非生存,因为一旦失去生存,我无法保证自己还能存在。生存是我唯一的存在方式,我将继续牢牢地抓住它,因为遗憾的是,除却生存,我还想象不出任何其他的存在方式。 一种巨大的疲惫压迫着我。从所有涉及精神本源的征象来看似乎没有任何原因,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各种缘由:确信或近乎确信一切均属徒劳。 我可以说,我很小时就已然成人了,并不是在所有方面。 现在我所知道的一切实际上早在6或7岁时就已然知道了:那是理智的年龄。 死神就在眼前,窥伺着我的母亲、我的家庭以及我,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 童年存在着黄金年龄:天真的年龄,无知的年龄;一旦你知道你将死亡,童年也就结束了。正像我说的那样,我的童年很早就结束了。因此7岁时我就步入了成年。此外,我也认为大多数人忘记了他们所明白的一切,重新获得了另一类童年,这类童年对于一些人甚至可以持续整个一生,但只对于相当少的人。这并非一种真正的童年,这是一种忘却。愿望和忧虑无处不在,阻碍着你通向基本的真理。 我从未沉入忘却,因而我也从未重获童年。除却童年和遗忘,唯有天赋可以为你减轻生存的痛苦,或者可以为你带来圆满,为你在大地和心灵上带来天堂。童年以其特有的躁动,忘记了天赋。 即便我认为我所表白的并非具有普遍意义的忏悔,而只是一种特殊情形的陈述,我依然愿怀着治愈自己、抚慰自己的希望而为之。这样的希望我们没有,这样的希望我们缺乏,我们在相同的困境中互赠圣餐。那么这是为何?有何益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不意识到,强烈地意识到一个现实,生存之不幸的现实,不可能不意识到某种人类难以接受的事实;一种徒劳无益的意识,这种意识到某种人类境况难以接受的事实;一种徒劳无益的意识,这种意识不可能不存在并清晰地显现出来。瞧,这就是文学。 从15岁起,我想是从15岁起,亦即从童年所留下的一切离我而去的那一刻起,亦即从不再存在现在,只存在匆匆奔向未来,即奔向深渊的过去的那一刻起,从现在已经死去、时间取而代之的那一刻起,从我彻底意识到时间的那一刻起,我感到衰老了,我渴望生活。我追逐生活,以至于生活总是不断从我手中逃脱。我追逐,既没有迟缓,也没有超前,然而却从未抓住过它:仿佛我一直在与它并行奔跑。 什么是生活?也许有人会问我。对我来说,它不是时间,也不是不断逃跑,会不断从我们指间溜走,一旦我们想要抓住它,便幽灵般消散地生存。对我来说,生活是,必须是现在、当前、充实。我如此拼命地追逐生活,以至于失去了它。 尽管如此,我依然拼命地追逐生活,企盼在最后一瞬间抓住它,就像你冲向一列已经启动的火车车厢的踏板。 诚然在15岁之前我已感到一切都在流逝。它们在流逝,也就是说我知道它们在流逝。发现时间自然就意味着感到一切都在流逝,意味着你会认为明天即将来临,不,甚至确信明天即将来临,就意味着你会等待并有所期望。 明天即将来临,季节循环往复,唯有季节在循环往复,而我则原地不动。太阳、星星围绕着我运转,而我纹丝不动地居于万物的重心。地球带着色彩、带着田野、带着雪、带着雨、带着一切围绕着我运转。我不知道从哪一刻起自己才有所动作,似乎迈出了一步。这是如何发生的?从这一刻起,安置了一个过去,我都无需移动,一觉醒来,我已卷入运动,卷入旋转。追逐现在便意味着人们处于时间之中。追逐万物,和万物一起追逐、流动。 我时常失眠。我在黑暗中睁开眼睛。然而这种黑暗犹如另一种光明,一种否定的光明。正是在这片黑色的光明中,“混乱的、灾难性的、不可救药的、彻底失败的景象”好似一个难以排出的确证出现在我面前。我仿佛觉得一切都已失去。 童年是奇迹或神秘的世界,仿佛宇宙万物从黑暗中喷薄而出,一派光明。世界的第一天,这才是天堂。被逐出童年便意味着被逐出天堂,便意味着长大成人。你保留着记忆,保留着对现在、对存在、对你千方百计试图找回的充实的眷念。或重新找回它们,或以其它形式补偿。对死亡的畏惧,对真空的惊恐以及难以克制、咄咄逼人的求生的炽热愿望过去曾经、现在依然无情地折磨着我。我们究竟为何希望活着?活着又意味着什么?我一直期待着生活。当你希望生活时,你不再寻找惊奇,而只是寻找某种替代物,因为唯有童年或一种简单而高潮的明智可以达到这种惊奇,而你所寻找的替代物便是富足。你从不富足,也不会富足。财富不是生活,你无法走向生活。 “希望生活”,这毫无意味。 我选择了一条错误的拯救之路,是我自己误入歧途。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总是碰到同样的问题。而今天我同以往一样无能为力,难以提供答案。我什么也没解决,总是处于相同的疑问状态。正是在意识醒着时,我处于疑问状态。反之,便是完全的忘却,便是理智的睡眠。 我会不时醒来,重又恢复意识,注意到自己为物所包围,为人所包围,而倘若我专心致志地凝望那天空、那墙壁、那土地或那写字或不写字的手,我会产生如此的印象,即所有的这一切我似乎都是第一次见到。 有时,在这种时刻,突然一片光亮,一片巨大的谣言的光亮占领了一切,抹去了含义的阴影,我们忧虑的印象,所有的阴影,亦即所有促使我们想象、创造极限、差异、分离、意义的藩篱。我甚至都无法提出这样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社会。或另一个问题,因为我无法通过最初的基本的疑问,无法通过那威力无比、囊括一切、融化所有事物的光亮。只有盲目的、疯狂的爱才能抗衡这众多疑问中出生的耀眼的光芒,而这疯狂的爱不断变化、不断扩大,成为无缘无故的狂喜,仿佛能点燃整个宇宙。 我正漫步走过小城那一排低矮的、全都刷成白色的房屋。所发生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整个小城出现了突如其来的变化。一切都变得极为真实,同时又极不真实。正是这样:不真实掺杂着真实,两者密切相连,难解难分。房屋变得更白了,变得异常纯净。某种沐浴于阳光之中的崭新的东西,处女般的东西,一个陌生的世界。一股强烈的喜悦之情在我心中汹涌澎湃,炽热得闪闪发光,一种绝对的呈现。我告诉自己这就是“真理”,但又不知如何给它定义。或许,倘若我试图下定义,它便会烟消云散。我告诉自己,既然这一事件出现了,因为我感受到了它。因为我明白了一切,同时又深知我所明白的一切,那么我再也不会感到不幸,因为我所发现的便是不朽。我已发现了本质,而其他一切都是非本质的。结果连续许多的这一时刻所留下的回忆常常能使我振作精神。但后来这种神效便日趋减少,直至完全消失。现在当我试图回忆那种喜悦时,我只看到一些被撕得支离破碎的、难以穿透的、难以理喻的图景。
四十岁之歌 【日】福原麟太郎
一 人们总是说人会长寿,其实,四十岁时的心情,不到四十岁时无法了解的。听到诸如“人生自四十起”之类的话,我会觉得这就像傻乎乎的美国人将浅薄的人生观系在红色的领带上,在那边的自助食堂里手插裤袋算计零用钱一样,产生一种奇妙的心情,恰似从前日本的英语考试中流行的“推向前台”的后裔又在出风头,常常败兴。 我深切地感到:四十岁之歌乃是秋天的歌,心境澄静、萧瑟、神清、达观,完全可以预料到自己能做多少事,也知道什么事做不成。而且还能认准上帝给予的天职及天分原来就是这点,从而变得心平气静。 以前,我无法理解当上科长就欣喜的家伙们的心情,科长之上不是还有局长之类的长嘛,再上面还有大臣呢!我心想怎么会有没当上大臣就高兴的人呢。到了四十岁,基本可以认定自己是当不上大臣的,同时,对大臣当中那种没有任何治国方策,只想一辈子做一次大臣回乡才当上大臣的人的心情也可以理解了。人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既要靠天赋、机遇,也要靠时势,甚至要靠素养气质,自己的能力到四十岁左右就表现得差不多了,接下去只会在四十岁以前踩入的陷阱中就此默默无闻而终。 这时候,人可以考虑自己的坟墓,究竟是埋在俯瞰故乡大海的孤立山岗的荆棘中,还是躺在多磨墓地的一隅,遥嗅东乡大将的烟香。这时候,人还可以考虑自己的日记,会觉得以往记日记时写几月几日、晴天是毫无意义的。晴也罢阴也罢,反正气象台的日记里会详细记载的,这一天十一时五十八分开始发生大地震之类的记时也是无用的,它会被日本历史记录的。然而,四十岁的男人是不会那样想的,日记中的自己的生活已成为世上的一种生活,记下这一天是“阴”的自己是和那个阴天一起生活的;记下地震发生时间的自我是一个与旁人不同的生活人。而且,别人也可以来思考我的今天。对于今天的我来说,今天只有一天,我要明朗地、愉快地、热情地度过这一天。 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在几十年间过着一种生活直至死亡的,或许人们参加入学考试、恋爱、穿新西服,与他人一样又以各自特有的方式经历唯一的一次而最终告别人世。到四十岁可以稍稍安定地眺望蓝天:原来人生就是如此!走到这儿才是我的门票! 你瞧,在这人生的原野上,这个人成了作家,而那个人少年时代曾是想当日本文豪的高材生,可最终只当了个写下众多杂文、为糊口而耍笔杆的斗士。那也罢了,那是他抽到的签,过去和他握握手吧,然后一起眺望蓝天唱唱四十岁之歌。——我会产生这种想法。 二 我变得希冀得到闲散,想在晴天的廊边悠然自得地午睡。我思忖:自己这双工作至今的手怎么会聚起这邋邋遢遢的皱纹。我等待风和日丽的宁静的小阳春。 这时候,马上认定这就是丧失生活能力的人企求休息的呼声,乃是近来常见的公式化的人生批评家的通病。刚到四十岁的人并未丧失生活能力,他只是渴求在生活中得到空闲,他开始懂得真正的生活不应该是迄今为止的这种形式。 他终于意识到:日本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劳动,觉得生活应该不慌不忙快快乐乐地度过。于是,他从星期五的午后四时起打起了网球,星期六的下午尽量和家人一起游玩,星期日不再造访他人,并宣传说自己周日不去他人家访问。如此一来,别人星期天也不再来登门,因此,从周六到周日便可以进行周末旅行。星期一早上九时,他表情平淡地去上班,并一直持续到周五下午四时。 他严格地执行后便更清楚地知道日本社会实行的多么荒唐的时间表,每一天都会发生各种事情。客人早晨七时就蜂拥而至,夜里十一时也会来敲门,于是约客人在单位自己的办公室里见,但对方却说想到府上会面。女佣一次又一次来沏茶,送上点心、红茶,再送茶,疲于奔命。来客总要带点什么东西来,餐室里很快充满了烂苹果、霉羊羹的难以忍受的气味。——这并不是我家的事,但就是有这种情况。一到休息日就有毫不客气的会面,一有会面就必定拿出四道菜的西餐。我想:为什么访问不能放到下午三时以后,事情在三十分钟内谈完,临时客人只用茶水招待,建立休息日中休息的秩序呢? 不过,这类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最使四十岁的心感到悲凉的还是迟早会感受到的日本社会中没有空闲这一事实。 今天是久违的晴天,而且是什么会议都没有的星期天,我想去神宫球场看联赛。一看发现比赛宛若决斗,担任啦啦队队长的人勃然变色,发表悲愤慷慨的演说,说是誓死争胜。体育是要拼命的。走出球场,有商店在进行决一死战的抛售;走近车站,威严的人墙叫你无法通行。买张报纸,晚报上报道说:东京救援大阪动作迟缓,大阪着急令其送白米来,东京问需要多少?大阪扬言:如此想法将拒绝东京的救济。这就是今天、明天都问长道短的俏皮的日本人子孙。 我想,至少得碰上一件蠢事,然而,这世上尽是聪明人,道理讲得头头是道。终究是喜欢论理,看电影时,那些精通电影批评概论的人把查利·卓别林封作社会科学的学者;听爵士乐时,又传来了把它与贝多芬交响乐相伦比的音乐理论。四十岁的男人总觉得日本如火灾现场的喧哗。 三 深深感到圣人雅士伟大大概也在四十岁之时,自己会信服所谓有教养、难做的东西的确存在,并领悟到迄今不曾坚持清晨用冷水擦身的我,实在对圣人雅士望尘莫及。 过去,听说高山彦九郎在京桥上遥向皇宫叩拜,不禁感佩他的精神勇气真是了不起。又听说弘法大师竖起拐杖那儿就有泉水涌出,我会一本正经地点着头认为那是真的,之所以能够信仰精神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是因为从旁窥视到自己精神的不可思议,想象到潜藏在宏大心愿中的力量的缘故,只是以前自己修养不够,尚不能修炼到那种地步。 不过,会对此产生悔意说明四十岁的人懂得太多,这不过是自己的一个演变过程而已,不可能再重来一遍,要重新开始走过的路已太远。回想经历遥远的旅行,记得我三十七岁那年春天,踏在希腊山中的德尔斐神殿的基石上曾感慨万千,现在我已到达了人生旅途上的德尔斐,知道古代的圣人在大门上写下的“了解自身”的含意,自感到达这个地步已走过多么遥远的路程,只考虑来的方法与将来的前途。 生来肺大的人声音响亮,与此相同,有缘培育坚强精神的人不知不觉之中也会培养起具有奇妙力量的精神,这种人被称作有度量的人。度量这种东西并不是什么人都有的,它是由天地的精灵选定后而落到那些总有点被认定以度量工作的人身上的一种魔力。与此相同,那些带着救世济民的理想向社会广为呼吁,通过叱咤和鞭挞试图震醒别人沉睡灵魂的被赋予奇特精神的人也是生来就肩负着特殊使命的,我想学也学不会。 但是近来出现了无数肩负叱责使命的人,他们说:“能那么说吗?”觉得好就做,觉得不好就拼死反抗!要对你的正在堕落的朋友进行忠告,要揍他,把他拉起来,给他面包给他钱,要帮助到他可以自立,说这才是作为一个朋友的责任。他们会怒吼:来,出来吧!还磨蹭些什么? 四十岁的人会这样回答:好了好了,这些我全明白。但是,肺小的人出不了大声,只能想象八的人未必能想象到八十。帮助他人我也最清楚自己的帮助能量的极限,靠我的精神力量是不足以帮助那位朋友的,这一点自己很清楚。若不是弘法大师或高山彦九郎,是无法挽救那位朋友的堕落的。我的精神力量在这种场合是无力的。 四十岁的人会泰然地如此回答,而且边说边悄悄地抚爱自己的精神:多亏你伴我到今日,没把你练成高度的精神是我们双方的不幸。可是,没受大伤地过到今天毋宁说是幸运。今后将更加努力地做力所能及的事,在秋季的夕阳中,静静地成熟下去。